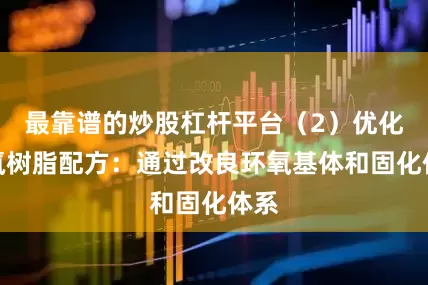图片
家常菜,比如炒土豆丝,谁都会做,谁都吃过,可要真炒到火候恰到好处,色香味俱全,让吃过的人念念不忘,那就不容易了。《黄鹤楼》就是这么一盘“顶配”的土豆丝,看似平常,实则功夫深厚,味道绝了。
一千多年来,围着这首诗,那真是口水官司不断。最有名的段子,就是说李白,“诗仙”啊,那么大的名头,跑到黄鹤楼,也想题诗,结果看到崔颢这首,愣是给憋回去了,留下一句: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这话是真是假,是后人编排,还是确有其事,咱们先不去细究它。但这事儿本身,就像给这首诗镶了金边,让它更显“厉害”了。
图片
还有更厉害的。宋朝有个叫严羽的,写了本《沧浪诗话》,挺有名的评论集子,里面直接把《黄鹤楼》捧为“唐人七律第一”。乖乖隆地咚,这评价可了不得!唐朝那是诗的国度,七言律诗更是唐诗里的“硬通货”,讲究平仄对仗,规矩森严。杜甫老爷子写七律,那叫一个炉火纯青,人称“律圣”。怎么这“第一”的帽子,就戴在了名气似乎比李杜稍逊一筹的崔颢头上了呢?
这就惹得后人嘀嘀咕咕了。有人扒拉这诗的“毛病”,说你看,头四句里,“黄鹤”俩字儿翻来覆去用了好几回,不嫌腻歪?第二联“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”,跟第一联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”,在平仄上没对上,这叫“失粘”,犯了律诗的大忌。
还有,“空悠悠”的“空”,跟上句“空余黄鹤楼”的“空”,意思也太近了,叫“犯复”。按说,写格律诗跟老木匠做榫卯似的,得严丝合缝,差一分一毫都不行。崔颢这几下子,看着有点儿“野狐禅”的意思。
可偏偏,就是这些看着不合规矩的地方,让好多人觉得,这才是真情流露,天然去雕饰。说这叫“不以辞害意”,感情到了那份儿上,奔涌而出,什么格律平仄,先顾不上了。这就像看一个性情中人,高兴了就大笑,难过了就抹眼泪,不藏着掖着,比那些四平八稳、说话滴水不漏的,反倒更让人觉得亲近、可信。
这就奇了。一首似乎“不守规矩”的诗,怎么就能得到这么高的赞誉,甚至压倒了无数名家名作?它到底好在哪里?崔颢写它的时候,心里到底在琢磨些什么?这背后,是不是藏着比诗句本身更深长、更曲折的故事?这一连串的疑问,就像黄鹤楼下那悠悠的江水,带着点儿神秘,也带着点儿诱惑,让人忍不住想往深处探一探。
一、从汴州才子到江楼过客:崔颢与他身处的时代一般理解,《黄鹤楼》就是一首登高望远、怀古思乡的诗。诗人先是由黄鹤楼的传说,引发了对岁月流逝、仙人不再的感慨;接着描绘了眼前长江两岸开阔而充满生机的景色;最后在傍晚时分,触景生情,抒发了浓浓的思乡之愁。整个过程,从怀古到写景,再到抒情,脉络清晰,情景交融,语言也自然流畅,毫无疑问是首好诗。
这个理解,对不对?当然对。这是这首诗最外层、最直观的意思。就像咱们看京剧,首先看到的是脸谱、服装、身段、唱腔,这是热闹,是规矩。
但这出戏到底好不好,还得看它背后有没有更深的“戏肉”,有没有唱到人心里去。要品出这《黄鹤楼》更深的“戏肉”,光看这“标准照”怕是不够,还得去翻翻它的“底片”,看看拍照片的人——崔颢,他当时是个什么状态,他按快门的那一刻,心里头都装着些什么。
要深究《黄鹤楼》的滋味,就得先认识一下崔颢这个人。
崔颢,汴州(现河南开封)人。生卒年不太确切,大概是唐玄宗开元初到天宝十三载之间(约公元704年 - 754年)。他年轻的时候,那可真是个“人物”。《唐才子传》里说他“资质俊美,风流倜傥”,不仅长得帅,还有才华,二十来岁,开元十一年(公元723年),就考中了进士。要知道,那可是开元盛世,唐朝的鼎盛时期,文化繁荣,人才辈出。能在那样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,绝对是人中龙凤。可以想见,那时的崔颢,大概是鲜衣怒马,意气风发,前途一片光明。
图片
他早期的诗,流传下来的不算多,但能看出来,风格是比较华丽、轻快的,喜欢写些宫廷生活、闺阁情思、边塞游猎之类。比如《长干曲》:
君家何处住?妾住在横塘。
停船暂借问,或恐是同乡。
写得活泼自然,很有民歌风味。
还有写闺怨的《王家少妇》:
十五嫁王昌,盈盈入画堂。
自矜年最少,复倚婿为郎。
把小女子的娇憨得意写得活灵活现。
然而,崔颢的仕途,并不像他中进士时那么风光。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很零散,只知道他大概做过太仆寺丞(管皇家车马的副职)、司勋员外郎(吏部下一个司的副长官,负责官员等级勋爵事务)等官职。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里甚至都没有他的正式传记,只是在别处零星提及。
这说明他在当时的官场上,地位并不显赫。跟那些官至宰辅、名动朝野的大佬比起来,崔颢顶多算是个中下级官员,而且似乎还不太得志,有“累官不进”的说法,就是说干了挺久,官位却没怎么升迁。
甚至还有记载说他“好蒱博,嗜酒,娶妻择美者,稍不惬即弃之,凡易三四人”,说他好赌好酒,婚姻上也不太检点,娶媳妇专挑漂亮的,稍微不满意就休掉,换了好几个。这话未必全是真的,可能有后人的附会或偏见,但多少也反映出他可能不是那种循规蹈矩、谨言慎行的“标准”官员形象。
那么,问题来了,一个才华横溢、年少成名的进士,为什么在官场上混得不尽如人意呢?
原因可能很复杂。也许是他性格确实有点放荡不羁,不为官场规则所容?也许是他运气不好,没遇到赏识他的伯乐?也许是他站错了队,得罪了权贵?
更重要的,可能还要看他所处的时代背景。崔颢的主要活动时期,是开元和天宝年间。开元前期,玄宗励精图治,确实是盛世景象。但到了开元中后期,尤其是天宝年间,情况就起了变化。唐玄宗渐渐沉溺于享乐,任用了像李林甫、杨国忠这样的奸相。
图片
崔颢的“累官不进”,会不会就跟这个大背景有关?他是不是那种看不惯李林甫之流,或者不屑于与之为伍,因而受到排挤的正直文人?史无明证,我们无法断言。但可以想象,一个有才情、有抱负的人,身处那样一个表面辉煌实则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,眼看着朝政日非,自己又无法施展才能,心里会是什么滋味?大概是既有对现实的不满,也有对未来的忧虑,还有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和无奈吧。
这种复杂的心情,会不会投射到他的诗歌创作中?
二、仙鹤、空楼与一缕乡愁《黄鹤楼》的具体创作时间了历来争论很多,没有一个确凿无疑的结论。但现在大多数学者,比如闻一多先生、傅璇琮先生等,都倾向于认为,这首诗不是崔颢早年得意时的作品,而是他经历了仕途的坎坷和人生的风雨之后,在中晚年时期,大约在开元二十年至天宝初年(公元732年 - 742年左右)写的。
傅璇琮先生在《唐才子传校笺》中考证,崔颢在开元二十二年(734年)左右曾任太仆寺丞,之后可能在京城与外任之间辗转。而黄鹤楼所在的鄂州(今武汉武昌),是当时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。崔颢完全有可能在某次因公出差,或者被外放、调任的途中,路过此地。
图片
这个时期,崔颢大概四十岁上下。这个年纪,少年锐气已消,人情世故也看得更透,对人生、历史、社会有了更深沉的体味。这个时间段,也恰好是开元盛世由顶峰开始显露疲态和隐忧的时期。
咱们先来感受这首诗:
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
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。
日暮乡关何处是?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这句用了个典故。三国时期蜀汉四相之一的费祎,死后成仙,曾经骑着黄鹤到这儿歇脚。后人为了纪念他,就给此楼取名叫黄鹤楼。别人会写如何登楼,风景如何壮丽,可崔颢第一句就出乎意料,“昔人”和他的黄鹤都“去”了,“此地”只剩下“空余”一座黄鹤楼。就像一部电影,刚开场,就看到剧终,崔颢一上来就说,都到了?那就散了吧。
图片
想象一下,崔颢登上了黄鹤楼,他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、指点江山的汴州少年,而是一个在宦海中沉浮多年、心事重重的中年过客。
那缥缈的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的传说,会不会让他联想到自己曾经的理想,或者那个看似辉煌却可能正在悄然逝去的盛世?它们是否也像那仙人黄鹤一样,“一去不复返”了呢?
《庄子·逍遥游》里说:“若夫乘天地之正,而御六气之辩,以游无穷者,彼且恶乎待哉?”那是何等的自由!可现实中,自己却处处受限。
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
崔颢接着感慨。那仙鹤啊,是真的不回来了,断了念想。天上能看到的,只有白云。这云彩啊,飘啊飘,飘了一千年,还是老样子,慢悠悠的,无拘无束,但也显得空旷、遥远,抓不住,留不下。“空悠悠”这三个字,把时间和空间都拉得特别开阔,让人心里也跟着空落落的。
图片
白云看似自在,实则随风飘荡,没有根基。这像不像自己在官场中的状态,身不由己,沉浮不定?又像不像历史长河中无数个体生命的缩影,看似存在过,却最终“空悠悠”,不留痕迹?
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。
然后,视角从上往下移,开始看眼前的实景。这天天气不错,阳光明媚。江对岸汉阳城那边的树木,长得什么样,一棵棵看得清清楚楚。江心里头,有个叫鹦鹉洲的小岛,上面长满了茂盛的青草。
图片
落日,长河,树木,芳草,岁岁枯荣,生生不息。说的是自然的永恒,可叹的是人生的短暂。
这鹦鹉洲也有个典故,据说东汉末年有个很有才华但脾气很冲的名士叫祢衡,就是那个光着膀子击鼓骂曹操的家伙,他曾经在这儿写过一篇《鹦鹉赋》,后来被人杀了,这洲就因此得名。
祢衡,一个才华盖世、但恃才傲物、最终死于非命的文人典型。《后汉书·祢衡传》记载他被黄祖所杀,“时年二十六”。崔颢写到这里,会不会抚今追昔,联想到祢衡的命运,进而感叹才华与命运的错位,甚至为自己的前途感到一丝寒意?这生机盎然的景色,反而可能勾起了他更深的忧虑和伤感。
日暮乡关何处是?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最后,写到时间,是“日暮”,太阳快下山了。黄昏时候,人站在高处,望着远处,最容易多想。
图片
这个“愁”,绝非简单的思乡之愁。它是一种复杂的、弥漫性的情绪。它包含了对时光流逝的惆怅,对个体渺小的喟叹,对理想失落的伤感,对前途未卜的忧虑,对世事无常的无奈,甚至可能还隐含着对时代隐忧的一丝敏感。那浩渺的江水,那迷蒙的烟波,既是眼前的实景,更是诗人内心状态的完美投射,而所有的感慨、迷茫、失落、忧愤,都凝聚成了那一句“烟波江上使人愁”。
三、千古一愁,何以共鸣?那么,崔颢在《黄鹤楼》里,到底想要表达什么?仅仅是个人的一点牢骚和乡愁吗?如果只是这样,恐怕难以承受“唐人七律第一”的盛名,也难以让后人传诵千年。
要回答这个问题,我们可以问问李白,为什么李白在看到崔颢的诗后,会发出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”的感叹?
图片
你想想李白那个人。“诗仙”啊,好像成天不是在天上飞,就是在跟月亮喝酒。可他也是个人,活在地上,有七情六欲,也有他的不得意,他的茫然。他一辈子到处跑,“仗剑去国,辞亲远游”,看起来潇洒,可心里头那点儿“找不着北”的感觉,怕是比谁都深。官场上,他想大鹏展翅,结果呢?碰了一鼻子灰,“赐金放还”,客客气气地把你请出长安城。说白了,就是“用不上你这号人物”。
他跑到黄鹤楼这儿来,可能也是旅途中,或者心里头正有点儿不痛快,想登高望远,舒散舒散,顺便写首好诗,显显他李太白的本事。这楼,这江,这景,多阔气!正憋着一股劲儿呢。
结果一抬头,看见崔颢那首诗。
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心里头“咯噔”一下。是啊,神仙都走了,留下个空架子。这不就跟我李白似的吗?抱着经天纬地的本事,结果呢?长安城里没我的地儿,空落落的。
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
唉!过去的风光,回不来了。就像那开元盛世的好时光,好像也在慢慢变味儿。眼前能抓住的,就是这飘来飘去的白云,看着自在,其实没根。我李白不也像这白云吗?四处飘荡,看着逍遥,心里头那点儿空落落的滋味,谁知道?
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。
景是不错,树是树,草是草,清清楚楚,生机勃勃。可那祢衡的下场……我李白这脾气,这不羁的性子,在长安不也得罪了不少人吗?这眼前的生机,跟我这心里头的隐忧,一对照,更不是滋味了。
日暮乡关何处是?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这句,怕是真戳到李白心窝子了。他老家在哪儿?也有说是西域,也有说是蜀中,反正离这儿都远着呢。可这“乡关”,对他来说,怕不光是地理上的家。更是精神上的归宿啊!他一辈子好像都在找,找那个能让他施展抱负的地方,找那个能懂他的人,找那个能让他心安的“家”。可找到没有?好像总是在路上,总是在怅望。这傍晚时分,看着这茫茫江水,迷迷蒙蒙,心里头那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“愁”,那叫一个铺天盖地!
李白读着这诗,估摸着不是在想“这平仄对不对”、“这用典好不好”。他是在想:“乖乖,这不就是我李太白现在心里头转悠的那些个念头吗?一句句都像是从自己心里掏出来似的,连那点儿说不清的滋味儿都一模一样!”
人家崔颢,已经把此时此刻,他李白心里的那份怅惘、那份失落、那份茫然、那份挥之不去的愁绪,用最熨帖、最自然的字句,给清清楚楚地摆在那儿了。就像你心里哼着一个调子,正觉得挺好,一抬头,发现旁边有个人,已经把这调子用最好的乐器,给奏出来了,而且奏得正是你心里想的那个味儿。
这时候,你还能干啥?
你还能拿起你的破锣嗓子,或者你的二胡,再去唱一遍、拉一遍吗?没那个必要了。人家已经替你唱出来了,唱得还那么好。你心里头,可能有点儿服气,有点儿泄气,还有点儿……惺惺相惜。觉得:“得,这位,是真懂我此时此刻的心思啊。”
所以,李白那句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”,可能不光是佩服崔颢的才华,更是一种深切的共鸣。在那一刻,崔颢和李白,在历史的空隙中,在人生的际遇上,严丝合缝地对上了。这份“懂得”,比什么都重。所以,他放下了笔。不是不能写,而是觉得,此时此刻,最好的表达,已经被别人完成了。
天宝初年的某一天,夕阳正慢慢沉入西边的山峦。武昌城外的黄鹤楼,沐浴在金色的余晖里。一个四十岁上下的文人,独自凭栏远眺。
图片
江风猎猎,吹动着他的衣袍,也吹乱了他可能已经有些许花白的头发。他的目光,越过眼前奔流不息的长江,望向对岸清晰可见的汉阳树,望向江心那片绿意盎然的鹦鹉洲,再望向水天相接处,那被晚霞和水汽染得迷离恍惚的远方。
图片
楼下,是人间烟火,是市井喧嚣。楼上,是他一个人的寂静,和心中翻腾的万千思绪。关于汴京故里,关于长安朝堂;关于年少轻狂,关于中年落寞;关于神仙传说,关于历史兴亡;关于这壮丽的山河,关于这渺小而又沉重的自我……这一切,都像江面上那变幻莫测的烟波,纠缠在一起,分不清,道不明。
他或许站了很久,直到暮色渐浓,星星开始在天鹅绒般的夜幕上闪烁。
图片
然后,他可能找了个地方坐下,借着楼内或许昏黄的灯火,或者干脆就着月光,铺开了纸,蘸饱了墨。没有太多的犹豫和推敲,那些盘桓在心头许久的情绪,那些呼之欲出的句子,便自然而然地流淌到了笔端:
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……”
当写下最后那句“烟波江上使人愁”时,他或许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那一口气里,有解脱,有怅惘,有喟叹,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和苍凉。
图片
他大概不会想到,他此刻写下的这二十八个字,将会让这座楼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标之一,会让无数后来的文人墨客在此徘徊、吟咏、感怀。他更不会想到,一千多年后,人们依然能从他的诗句里,读到自己的影子,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孤独、迷茫与淡淡的忧愁。
《唐才子传·崔颢》载:“(颢)少年为诗,意浮艳,多陷轻薄;晚节忽变常体,风骨凛然。一窥塞垣,状极戎旅,奇造往往并驱江、鲍。尝游武昌,登黄鹤楼,感慨赋诗。”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配资平台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线上股票配资网站还是那最后大反转一出场!原本大家都凑在屏幕前
- 下一篇:没有了